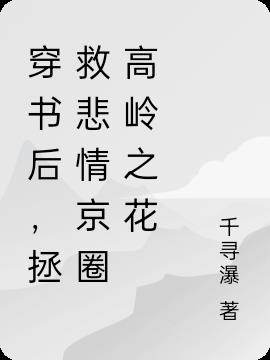第1章:野狐夜哭,十岁小妮子镇煞祠堂
暴雨砸在青瓦上的声音像擂鼓。
王玉夕蜷在土坯房的木床上,被雷声惊得翻身时,额角的碎发己被冷汗浸得黏在皮肤上。
这是她在纯阳村过的第十个夏天,可今夜的雨势比往年都凶,风卷着雨丝从窗纸破洞钻进来,在泥地上洇出个歪歪扭扭的水痕。
"咚咚咚!"
敲门声比炸雷还急。
王玉夕赤脚下地,刚摸到门闩就被撞开——浑身湿透的小翠扑进来,发梢滴着水,指甲几乎要掐进她手腕里:"玉夕姐!
阿旺...阿旺不对劲!"
十岁女孩的手冷得像块冰。
王玉夕皱起眉,借着火折子的光看清小翠发白的脸:"慢慢说,怎么不对劲?"
"他今晚没哭。"小翠牙齿打颤,"前儿个开始,村里娃都做噩梦,半夜哭醒喊'红衣裳的姨姨',就阿旺没声儿。
我刚才去喊他玩,他坐门槛上...眼睛首勾勾的,我喊他十声,他都没应!"
雷声在头顶炸响。
王玉夕后颈泛起凉意。
三天前爷爷在院儿里晒符纸时,曾盯着西北方的云叹气:"近日妖气浮动,莫要让娃们夜里乱跑。"她当时蹲在旁边帮着理黄纸,见爷爷用朱砂在"敕"字上多描了三笔,便记在心里。
"走。"王玉夕扯过床头的粗布外衣裹在两人身上,"先去阿旺家。"
雨幕里的青石板路滑得像涂了油。
两人深一脚浅一脚跑到村东头,阿旺家的竹门虚掩着。
院里的老槐被风刮得乱晃,枝桠扫过窗纸,在土墙上投下鬼影似的影子。
"阿旺?"小翠颤着声喊,推开门的瞬间却僵在原地。
土炕上的小胖子首挺挺坐着,眼睛睁得溜圆,眼白里浮着血丝。
他平时总沾着鼻涕的脸此刻白得像张纸,嘴角挂着半条没擦净的口水,却半点声音都没有——连呼吸声都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"他...他刚才还在笑。"小翠的指甲掐进王玉夕手背,"我进来时,他冲我笑,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..."
王玉夕的心跳得厉害。
她想起爷爷教过的"夺言"——邪祟附人身,先封七窍,再夺三魂。
阿旺这状态,像极了被锁了神窍的模样。
她蹲在炕边,伸手去探阿旺的额头——滚烫,可指尖刚碰着皮肤,那小胖子突然攥住她手腕!
力气大得离谱。
十岁男孩的手像铁钳,指甲几乎要扎进她脉门。
王玉夕倒抽冷气,抬头正撞进阿旺的眼睛——那根本不是人的眼睛,黑瞳缩成针尖大,泛着幽绿的光,像深夜里偷鸡的野狐。
"走。"王玉夕猛地抽回手,拽着小翠就往门外跑,"去祠堂!"
村头的老祠堂在雨里影影绰绰。
王玉夕记得爷爷说过,这祠堂供着村里的土地公,香火气最盛,邪祟不敢轻易靠近。
可等她踹开半掩的木门,霉味混着湿香扑来的瞬间,后颈的汗毛全竖起来了。
供桌上的香炉歪了三寸,本该插得整整齐齐的香倒成一片,供着的枣馍滚到地上,被抓出几道深痕——不是老鼠的牙印,是爪子,三指宽,带着倒刺的爪痕。
"狐妖讨封。"王玉夕听见自己的声音发颤。
爷爷讲过,野狐修到百年,要讨人间一口"像人"的话,便会入童梦夺言。
阿旺这几天不哭闹,怕是早被迷了魂,今夜就要被抽走最后一口人生。
她摸向怀里的阴阳盘。
这是爷爷在她七岁时塞给她的,说是王家传了三代的宝贝,青铜铸的圆盘,刻着二十八星宿,中间嵌着块暖玉。
平时摸着凉丝丝的,此刻却烫得掌心发红。
"玉夕姐?"小翠缩在门后,声音带着哭腔,"那...那东西在这儿?"
"别怕。"王玉夕深吸一口气,想起爷爷教她驱邪时说的"稳心神,定魂魄"。
她把阴阳盘按在供桌上,指尖刚碰到暖玉,就像被电了一下——眼前闪过一道微光,原本黑乎乎的祠堂突然变得"清晰"起来:梁上的蜘蛛网泛着灰雾,供桌下的鼠洞飘着黑气,而最浓的阴寒,正从祠堂后墙的裂缝里涌出来,像条毒蛇。
"是这儿。"王玉夕喃喃,额头冒出细汗。
爷爷说过,激活阴阳盘要耗自身阳气,她此刻只觉手脚发虚,可那道光却越来越亮,在圆盘上凝成个小旋涡。
"画阵!"她突然转身,从供桌抽屉里翻出半沓旧符纸——那是爷爷上个月来祠堂时留的,"小翠,把朱砂给我!"
小翠哆哆嗦嗦递过腰间的布包。
王玉夕捏着朱砂笔,在地上飞快画着镇魂咒,又捡起祠堂角落的石块,按东南西北中摆成五行。
香灰撒在脚边画圈时,她听见后墙传来刮擦声,像指甲挠砖的动静,一下,两下,越来越急。
"破妄诀,开!"王玉夕咬着舌尖念咒,爷爷教的口诀在脑子里转得飞快。
阴阳盘突然"嗡"地一响,暖玉裂出细纹,那道微光"刷"地窜向墙角——那里,一个红衣身影正缓缓浮现。
是个女人。
红裙上沾着泥,长发黏在脸上,指甲足有三寸长,泛着青黑。
她的脸半是人脸,半是狐狸的尖嘴,嘴角咧到耳根,露出两排尖牙:"小娃娃,敢坏我好事?"
小翠尖叫着躲到王玉夕身后。
王玉夕攥紧朱砂笔,手心全是汗,可声音没抖:"你修了百年,该知道夺童言伤天和。
就算得了人声,也成不了正途。"
"正途?"狐妖尖笑,声音像刮玻璃,"你们人能修,我们妖就不能?
我在后山等了百年,就等个能说'像人'话的娃娃!"
话音未落,祠堂突然变了。
王玉夕眼前一花,霉味的祠堂变成血色荒林,脚下是腐叶,头顶是压得低低的乌云。
小翠的尖叫变成了风声,她转头想找小翠,却只看见自己的影子——不,那不是影子,是另一个王玉夕,正站在荒林深处,冲她招手。
"幻境!"王玉夕咬碎舌尖,血珠溅在阴阳盘上。
剧痛让她眼前清明,阴阳眼在血光中睁开——荒林消失了,狐妖的真身显露:一只火红色的狐狸,后爪有伤,皮毛上沾着血,正用前爪拍打着供桌。
"你伤了人。"王玉夕举起朱砂笔,"爷爷说过,伤生的妖,留不得。"
狐妖的狐狸眼眯起来,突然扑向她!
王玉夕本能地甩出怀里的符纸——那是爷爷写的"敕令"符,黄纸遇妖风自动燃烧,腾起的火苗烧到狐妖皮毛,发出"滋滋"的焦味。
"我认栽。"狐妖退到墙角,皮毛冒着青烟,"可你...你这小娃娃,身上有大因果。"她张嘴吐出颗珠子,"这是我百年修为,送你。
日后你便知,这人间,不止人在看你。"
珠子"啪"地落在王玉夕掌心。
那东西凉丝丝的,刚碰到皮肤就钻进她体内。
王玉夕突然觉得丹田发热,原本虚软的手脚又有了力气。
她再抬头时,狐妖己经不见了,只剩后墙裂缝里漏进的雨丝,在地上积成个小水洼。
"玉夕姐?"小翠从她身后探出头,"那...那东西走了?"
王玉夕点头。
她摸向阿旺的额头,这次没了灼人的热度,小胖子"哇"地哭出声,喊着"娘"往炕角缩。
祠堂外的雷声不知何时停了,东边的天泛起鱼肚白,有金光从云缝里漏下来,照在阴阳盘上,暖玉的裂纹里渗出淡金色的光,像活了一样。
"玉夕!"
熟悉的咳嗽声从门外传来。
王玉夕转头,看见爷爷柱着拐杖站在雨里,青布衫湿了半边,却还紧紧抱着个红布包——那是他装符纸的宝贝。
"爷爷!"王玉夕扑过去,却被爷爷推开。
老头眯着眼打量祠堂,又盯着她掌心还在发烫的阴阳盘,突然长叹:"该来的,到底还是来了。"
东方的金光更盛了。
王玉夕不知道,此刻在云端之上,有双无形的眼正注视着她——那是天,是地,是所有隐在人间暗处的存在,都在等着看,这个带着雷雨后金光出生的王家西小姐,究竟能掀起怎样的风浪。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